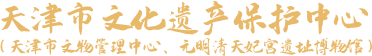《西青元宝岛:明清至民国时期墓地发掘报告》近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出版。著名考古学家陈雍先生为该书做序,现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资料性与研究性俱佳的“明清小墓”发掘报告
——《西青元宝岛:明清至民国时期墓地发掘报告》序
近二十年来,天津建设工程考古发现的明清民国时期墓地越来越多。这类墓葬都是小型土坑竖穴墓,俗称“明清小墓”,因其年代晚、规模小、等级低、数量多,在业内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2004年和2005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连续两年发掘蓟州区桃花园墓地,揭露出100多座“明清小墓”。在工地上,我们看着成片的“明清小墓”,寻思着如何提升研究这类小墓的学术含量,挖掘出更多的价值。当时想到的是人类骨骼考古学研究,为此请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李法军教授,对桃花园墓地200多个个体人骨标本综合研究。同时建立了天津古代人类骨骼标本库,目前已经收集天津地区出土的古代人骨标本1000多个个体,正在按墓地进行研究。
2020年以来,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继在西青区南运河沿岸揭露出元宝岛墓地、文化小镇墓地、大梁庄墓地,在北辰区北运河沿岸揭露出李嘴墓地。这些墓地的年代均为明代至民国时期,都是所谓“明清小墓”。我和遗产保护中心朋友多次交谈,“明清小墓”考古资料应当怎么整理研究,发掘报告应当怎么写才算得上好。
后来,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发了我对天津南北运河沿岸“明清小墓”的看法,[1]李法军教授也参加了讨论[2]。基于“乡土社会”这个概念,我将天津南北运河沿岸的这些“明清小墓”称为“乡土墓葬”。我提出,研究“乡土墓葬”特别需要加强墓地形态研究与人骨研究的结合,探讨以人骨为本位,以父系家族为重心,以村落墓地为单元的研究方法。李法军认为,从地域空间上,特别是从大运河沿岸来考虑家族墓地的确是一个突破口,这是一个极富建设性的视角。这个提法直接将有关明清时期墓葬的考古学分析引向了社会史研究,给了我们较大的学术提升空间。我们的这些想法,希望在以后的考古资料整理与发掘报告编写中得以探索。
依照南北运河沿岸墓地发掘的先后顺序,西青元宝岛墓地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最先提到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日程上来,要求在2024年内出版。
前面提到的明清小型墓葬研究方法,其前提条件是保存较好的成片有规律埋葬的墓地。元宝岛墓地遭到后代严重破坏,保存现状很差,成片有规律埋葬的墓葬数量不多,墓地布局与蓟州桃花园墓地、北辰李嘴墓地有所区别,研究这个墓地几乎无法做到“以父系家族为重心,以村落墓地为单元”。想要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发掘报告,最稳妥做法是按墓葬发表考古资料,这种发掘报告在业内已有先例,元宝岛墓地报告这么编写并无不可,然而负责元宝岛墓地发掘的尹承龙没有这么做。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边做田野考古及其他工作,一边整理研究元宝岛墓地资料。报告脱稿后,他虚心向多方请教,反复修改、补充,校样出来后还不断修改,最终写出了天津考古第一部资料性与研究性俱佳的“明清小墓”发掘报告。夏鼐先生特别强调,发掘报告的编纂是每一个发掘工作的最后一环节,只有发掘报告写成后,负责发掘的人才可算是完成了他的工作,主持发掘工作的团体,应该负担起推动编写报告和出版报告的任务。[3]夏先生提出的要求,负责元宝岛墓地发掘的尹承龙做到了,并且做得很好。
《西青元宝岛:明清至民国时期墓地发掘报告》主体部分由六章组成,第一、二章为资料部分,包括概述、墓地与墓葬;第三、四、五、六为研究部分,包括出土器物与墓葬年代研究、丧葬习俗研究、鉴定检测与研究报告、墓地研究。报告的第一至第六章记录了元宝岛墓地获取、分析、阐释考古遗存的完整过程。这里提请注意的是,元宝岛墓地发掘报告没有把人类遗存鉴定研究与金属人工制品检测研究作为考古报告的附录,而是作为报告的主体部分。
考古界长期以来,把田野发掘所获的人类遗存与自然遗存,作为田野考古报告的附录,是相当不妥的。我们平常所说的考古遗存,包括文化遗存、人类遗存、自然遗存三大类别,它们彼此之间不存在主次关系。因此在田野考古报告里,这三个类别的研究都应当属于考古报告的主体部分。[4]
《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5]是中国考古学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虽然距今已经90年了,但是对于今天考古报告编写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城子崖报告的体例结构是:第一章“城子崖遗址及其发掘之经过”,第二章“城子崖地层之构成”,第三章“建筑之遗留”,第四章“陶片”,第五章“陶器”,第六章“石骨角蚌及金属制器”,第七章“墓葬与人类、兽类、鸟类之遗骨及介类遗壳”;附录“城子崖与龙山镇”;图版目录,插图目录,表目录。这部考古报告将遗址所在地的历史沿革作为附录,遗址出土的墓葬与人类、兽类、鸟类之遗骨等则作为报告主体部分。从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的视角看,元宝岛墓地发掘报告的写法是田野考古报告的正确回归。
元宝岛墓地发掘报告通过墓葬丧葬习俗与墓地布局两个方面,推定出该墓地的属性类型。报告第四章“丧葬习俗研究”,把墓葬棺内发现的钱币、禅杖形簪、钮扣、材头钉及棺底草木灰和白灰,棺外发现的陶瓷罐、文字符箓砖瓦,以及二次葬,全部放到墓葬的“考古情境”里考察,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元宝岛墓地所反映的入殓、下葬、浮厝等丧葬习俗做出了复原,并且归纳出墓地的葬俗特点。这章的写法颇有意思,每一类遗物、遗迹先是叙述发掘所见,接着列举文献记载,最后将考古遗存及其现象结合文献记载进行讨论,进而复原有关葬俗。这么写,考古遗存及其现象就是“经”,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犹如“注”,报告做出的讨论仿佛“疏”,三个部分的逻辑关系加强了报告论证的说服力。
报告第六章“墓地研究”,把元宝岛墓地揭露的120座墓葬全部放到墓地的“考古情境”里,考察墓葬的空间位置、墓葬朝向、埋葬方式、葬具种类、随葬品组合等,由此推测出元宝岛墓地为若干未经规划墓群的组合;在考虑到元宝岛墓地主体年代与所处地理环境的前提下,结合有关历史文献记载,认为元宝岛墓地不见典型家族墓葬,其主体可能是清代至民国时期杨柳青中心城镇周边的一处中下层居民的义冢和攒柩(亦即浮厝)之所。
所谓“考古情境”,是一种认识与解释“过去”的方法或过程。这种研究方法或过程,通过提供一个多维框架,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考古遗址或墓地内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去理解过去的事物和现象,以达到复原社会历史的目的。这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过程,在元宝岛墓地发掘报告里有较好的呈现。
元宝岛墓地发掘与研究属于历史时期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发掘用的是考古学方法,这是毫无疑义的。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涉及到大量历史文献,用什么方法研究的确是个问题。我见到一些历史时期的考古案例,发掘用的是考古学方法,研究用的是历史学方法,好像京剧梆子两下锅的一出戏。是用历史文献辅助研究考古遗存,还是用考古遗存印证补充历史文献?从论证的角度来说,考古遗存与历史文献,谁是内证,谁是外证,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与做法。
我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方法都应当是考古学的,它是一种更综合的方法,将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按主次结合起来使用,更全面地认识与解释社会历史。这样的考古学或可称为文本辅助考古学(Text-aidedarchaeology)。文本辅助考古学研究特别强调文本与考古情境互映,文本存在于考古情境之中,考古情境也有赖于文本呈现与活化。
元宝岛墓地发掘报告认为,该墓地主体可能为“义冢和攒柩之所”。这是区别于传统父系家族墓地的另一属性墓地,对于研究天津“明清小墓”具有积极意义。我在发掘现场跟尹承龙说,这片墓地的分区,可以参考清道光年刊印的《津门保甲图说》,看看墓地能否与地上村落对应。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头脑里有父系家族墓地的想法,这个先入为主的想法给尹承龙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扰。但是他没有被先入为主的概念束缚住,而是从考古材料出发,最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至于这个墓地是否属于“义冢和攒柩之所”,还有研究空间。
我没发掘过也没见过古代义冢,关于中国古代义冢的知识来自文献。客死他乡或贫困者往往被埋葬于义冢,古代义冢的社会功能是对传统家族墓地的补充。一般认为,真正意义的义冢最早始于宋代,分为官方与民间两大类。晚明以降,民间义冢形成了不同种类,大体分为会馆建的同乡义冢、会所建的同行义冢、宗族建的同族义冢、慈善组织和个人建的贫民义冢。
按照晚明以来不同种类义冢反观元宝岛墓地。该墓地共揭露出120座墓葬,据人骨可以明确为男女同穴合葬墓39座,占总数32.5%,其中一男二女合葬墓4座。该墓地使用单棺墓60座,占总数50%;双棺墓49座,占总数40.83%;三棺墓葬8座,占总数6.67%;有棺墓葬共117座,占总数97.5%;无棺墓葬3座,占总数2.5%。该墓地随葬的首饰以银质为主,大部分表面可见鎏金处理,铜质首饰仅占少数,未见主体材质为金的首饰,部分发簪的簪头和簪杆为两种合金成分。仅据以上三个方面情况来看,元宝岛墓地可以排除贫民义冢,但是究竟是同乡义冢,还是同行义冢,或者是同宗义冢,均无从判断。
我们在探讨义冢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M73、M85、M90为二女性合葬墓,M84、M97为三女性合葬墓。M81出土印文:古柳王氏;M83出土砖文:登仕郎王公讳富德;M84出土瓦文:王母陆太君,出土另一瓦文:皇□例赠孺人王母太君;M85出土砖文:王母安太君,出土瓦文:清封孺人王二公讳廷杰继配□□。这些都是用“义冢”无法解释的。
受元宝岛墓地发掘报告的启发,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晚明以降,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与成规模人口流动,较发达地区城市(镇)的墓地,除了家(宗)族墓地、各种义冢,是否出现了城镇居民的公共墓地?这种墓地与近代城市(镇)的公墓不同,殆有近似的社会功能。
尹承龙在发掘报告的“后记”里,反思了因田野考古工作疏忽造成的信息丢失。由此体现出,通过考古资料整理与考古报告编写对于田野考古发掘认识方面的提高。另外,由于时间的关系,发掘报告对出土文物、人骨的研究尚存在着某些不足,报告的文字表述还可以仔细打磨。
读完元宝岛墓地发掘报告,我高兴地看到天津考古年轻一代的成长与进步,我很愿意将这部资料性与研究性俱佳的发掘报告推荐给更多的青年朋友。
陈 雍
2024年9月19日
[ 1 ] 陈雍:《天津南北运河沿岸的乡土墓葬》,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公众号,2021 年 8 月 9—11 日。
[ 2 ] 李法军:《关于天津明清小型墓葬研究的一点看法》,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公众号,2021 年 8 月 22 日.
[ 3 ] 夏鼐:《田野考古方法》,《夏鼐文集》(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 4 ] 陈雍:《考古何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 年。
[ 5 ] 傅斯年、李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