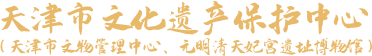编者按: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积极推进天津考古事业发展,强化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当下,本公众号日前推送了考古学家陈雍先生关于李嘴明清家族墓地人骨DNA研究和天津方言来源的学术随笔,引发广泛讨论。陈雍先生关注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在《考古的天津》等文章中“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天津历史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征。此次推送陈雍先生的文章《大运河、海河与天津城》。文中提出天津“枕山抱河、近都临海”的文化生态特征,并以宏观的学术视野作了历时性梳理,对认识天津历史文化具有重要启示。今后,本公众号将不定期推发相关文章,以飨读者。希望借此不断强化学科融合与方法论创新,跳脱出“就事论事”的浅表层面,多从文化结构或文化模式的角度观察问题,进一步发挥考古在历史文化研究与当今文化对话中的桥梁作用,增强文化自信,讲好天津故事。
大运河、海河与天津城
陈 雍
《天津日报》2025年4月21日“理论创新”专栏刊载白俊峰、尹承龙的《河城互动视角下的海河历史文化》,从“河城互动”视角,用“考古海河”话语,指出海河历史文化(天津地域文化)是距今4000年来人类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跳出“直沽寨—海津镇—天津卫”单线城市发展逻辑,从经济与军事两个维度,尝试构建一个自隋唐至明清的城镇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考察天津城市起源发展。文章提出,激活河与城的文化基因,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胸怀,在唤醒记忆的同时,建构新的叙事,是为研究海河历史文化的现实意义。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天津城市因河而生,依河而建,治河而安,用河而繁。在河与城互动中形成的海河历史文化,它的根深植在天津城。这篇文章摒弃了天津地域文化研究中的环境决定论,用文化生态研究范式解读海河历史文化。“文化生态”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文化生态”认为,人类是一个由文化和生物构成的系统,文化与生物的相互影响,形成共生关系,人类系统存在于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环境系统里。因此,可以通过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文化适应环境的动态过程及文化变迁规律。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适应特定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形成了特有的形态。
历史文献里有许多关于天津城市文化生态的内容。清康熙刊本《天津卫志·建置》记载,天津卫城开设四门,门上建楼。北门城楼,今(康熙十三年)改“北拱神京”;东门城楼,今改“东连沧海”;南门城楼,今改“南达江淮”;西门城楼,今改“西引太行”。天津卫城四个城门楼上的匾额题字就是明清天津城的文化生态。

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明代早期城墙基础
清代诗人冯培《晚次天津》这样描述天津城市文化生态:“霜清沙岸晚烟屯,析木津边气吐吞。星斗夜高天北户,蛟鼍秋压海东门。地通贡赋帆樯集,家擅鱼盐井灶喧。七十二沽称沃衍,由来左辅壮畿藩。”朱岷《初到天津》这样说:“潞卫交流入海平,丁沽风物久闻名。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

西青文化小镇发掘现场
天津又称为津沽、津门、三津,都是天津城市的文化符号。天津素有七十二沽的说法,“津沽”地名体现出自然环境特征。天津卫是京畿门户,“津门”地名体现出社会环境特征。天津东临渤海,又称为“海门”,实为国门。清代大沽炮台分别取“威镇海门高”其中一字命名。清道光刊本《津门保甲图说·县城内图说第一》:县城内分三卫:中“天卫”,左“左卫”,右“右卫”,“三津”地名体现出社会环境特征。根据上述明清天津城市文化生态,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枕山抱河,近都临海。

西青元宝岛墓地
我在《考古的天津》一文中提出天津古代文化遗存的两大特征:一个是越靠近北部山地(燕山)的遗存年龄越古老,越靠近南部海洋(渤海)的遗存年龄越年轻,反映了天津古代先民适应环境的大过程。另一个是,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由多元封国向一元帝国转化的重大转型时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天津地区得到第一次空前大发展;自辽金至元明,是北京发展为国家中心的重要历史时期,随着北京政治地位的提升,天津地区又一次得到快速发展,天津地区战国至元明时期古代遗存分布数量的变化,反映了天津古代社会发展和中国大历史脉动的耦合。

十四仓遗址2024年考古发掘区
公元10世纪,中国历史进入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以南北为轴心的争战时期。公元13世纪,以南北为轴心的政治格局形成后,与这个政治轴心平行的京杭大运河,成为连接中国北方与南方的文化线路,人流、物流、文化流源源不断从中国南方流向北方。位于京杭大运河与海河交汇处的天津(直沽),成为河漕与海运的重要交通枢纽。

明清天妃宫大殿基址
公元15-16世纪世界体系出现,中国开始有了海洋主权与海疆意识,构建起东部沿海自辽宁至广西的海防工程体系。海河入海口的大沽海防(大沽炮台、北塘炮台、北洋水师大沽造船厂),成为明清海防工程体系中最重要的北方战略节点。
公元13世纪以来,北—南向的大运河(南运河、北运河)与西—东向的海河(干流),在天津城市中间交叉穿过,不舍昼夜流向大海,塑造出中国北方最大的入海口城市的独特文化形态。

北辰张湾沉船遗址2号沉船出土现场
天津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在历史文化名城的语境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尽管“历史”与“文化”在具体语用上可以被分为两个方面,但是“历史”与“文化”的共生关系并没因此而改变。
天津考古在天津人类与自然(人地关系)、天津与中国(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天津与世界(中西文明冲突调适)不同时空框架下,从距今10万年以来的考古遗存中提炼出三个核心问题:天津人从哪里来?天津文化从哪里来?天津城市从哪里来?这三个问题的本质,是哲学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在考古学上的投射。天津考古提出的天津人、天津文化、天津城市,为研究天津地域文化提供了一个从历史到未来的完整叙事逻辑和话语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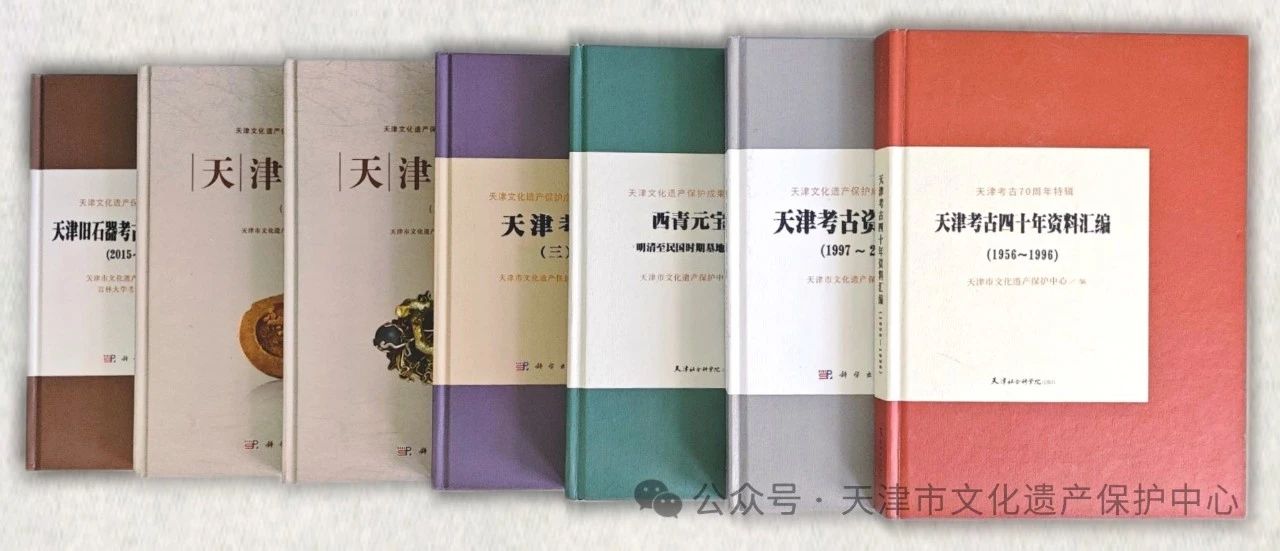
近年出版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