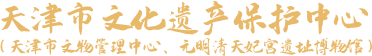编者按:日前,本公众号推送了考古学家陈雍先生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多学科考古学研究案例:天津李嘴明清家族墓地》一文。陈雍先生由人骨DNA研究延伸到天津方言岛现象,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他反复强调多学科融合和方法论创新在地域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现经本人同意,本公众号全文推发。
从李嘴明清家族墓地人骨DNA研究想到的
陈 雍
前不久,我写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多学科考古学研究案例:天津李嘴明清家族墓地》在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公众号推出后,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蔡大伟教授给我发来微信,我俩就李嘴墓人骨稳定同位素研究聊了聊。他说,不仅要研究46例女性个体的来源,还要研究男性人骨的来源。


实验室人骨古DNA 提取
他这句话对我有很大启发,发现自己凭自然思维做了个预设:一元的Y染色体单倍群男性是本地的,多元的线粒体单倍群女性是外来的。这里涉及到天津人的来源问题。
学界一般认为,天津是一个移民城市,天津地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是天津话,称天津为“哏儿都”。这种认识涉及到天津方言的起源问题。
当下,“天津方言岛”与“安徽起源说”,是学界主流意见。往往讲起天津方言都会提起“燕王扫北”,还有人依据文献提出明代安徽籍军官占有的比例来支持这一假说。
我认为,以往天津方言来源研究,是从现代方言的某些语音和词汇做出的比较,仅是语言表层现象一些契合。已有的天津方言研究方法论,大都是共时性语言比较,缺少历时性语言演变的实证,同时还缺乏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底层逻辑,通俗地说,语言离不开人。
元朝诗人傅若金《直沽口》云:远漕通诸岛,深流汇两河,鸟依沙树少,鱼旁海潮多。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通过诗人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元朝时,驻扎在海津镇的军人与直沽当地居民的语言交流融合现象。
“安徽起源说”作为解释天津方言形成的重要假说,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它提示了军事移民对于天津方言形成所起的作用。如果将这一假说作为天津方言来源的唯一解释,就把复杂的语言演变过度简单化了。

天津出土人骨体质人类学研究
由此我想到了李嘴明清家族墓地人骨的古DNA、稳定同位素、体质人类学研究。今后的天津方言来源研究,如能与考古学、生物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结合起来,构建一套完整的证据链,对于天津方言乃至天津历史文化研究,无疑是一种理论与方法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