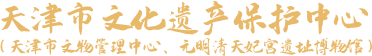编者按:李嘴墓地田野发掘完成后,我们对墓地出土全部人骨进行全基因组研究。考古学家陈雍先生指导田野发掘,参加验收,颇有思考并撰文。他一再说,写这篇小文不是挑毛病,而是希望大家对多学科结合给予更多关注,通过多学科深度融合,把墓地研究做得更好。现经本人同意,全文推发。
一个值得关注的多学科考古学研究案例:
天津李嘴明清家族墓地
陈 雍
2021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北运河畔的北辰区李嘴村发掘一处明清时期墓地,包括1座“明堂”遗迹和33座土坑竖穴墓,没有发现墓志或其他反映墓主信息的实物资料。共发现79具人骨,其中夫妻合葬最多,有双人、三人和四人葬,单人葬为数不多。墓葬均为南北向,“明堂”正上方(北)1座墓,其他32座墓分成两列位于“明堂”左右(东、西)两侧,呈雁阵“人字形”排列。(天津北辰李嘴明清家族墓地考古取得新发现,“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公众号,2022年2月4日 )

李嘴墓地全景
墓地“明堂”见于宋代《地理新书》,其位置中心是整个墓地的核心,因此“明堂”又称为“地心”,即墓地规划的坐标基点。每座墓葬选穴必须依据埋葬规则按男性死者的辈分与长幼,对照“明堂”确定具体穴位。考古发现最早的明堂为宋金时期,流行于明代,延续至清。北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发现了不同年代与类型的墓地“明堂”。目前,天津宝坻、武清、北辰、西青区发现了明清时期的“明堂”。

李嘴墓地明堂发掘现场
宿白《白沙宋墓》(宿白:《白沙宋墓》(第二版),文物出版社,2002年)认为,白沙一号、二号、三号宋墓按年代顺序下葬,呈三角形排列,位序符合宋代《地理新书》记载的“昭穆贯鱼葬”,根据墓葬题记和出土地券,确定墓主人姓赵,进一步支持了家族墓地的推断。该报告通过墓葬布局、年代顺序与《地理新书》等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首次在中国考古学上确认了宋代“五音墓地”的实例,开创了历史时期墓地研究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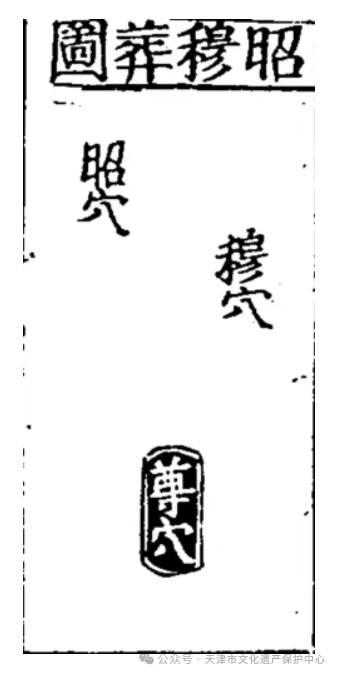
《地理新书》昭穆葬图
李嘴墓地发掘时,我去看过。墓地的雁阵“人字形”布局,很像《地理新书》的“昭穆贯鱼葬”。33座墓葬由北向南可分为11行,如果同一行墓葬的男性墓主为同一代人,那么整片墓地最多是11代。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同代男性(即兄弟)如果超过2人,同代墓葬排列则为2行或更多,在没有墓志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仅靠墓地布局及随葬品,难以推断出这片墓地具体是几代人。
为了研究这片墓地的埋葬规则、布局结构,以及墓葬死者的婚配模式、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合作,对李嘴墓地出土人骨进行DNA分析研究。
2024年10月18日,我应邀参加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的“天津市北辰区李嘴明清家族墓地出土人骨资料DNA分析研究”结项验收会。会前,我仔细阅读了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蔡大伟教授团队提交的李嘴墓地人骨全基因组分析报告,并且做了笔记。

李嘴墓地人骨DNA 研究验收会
该报告通过遗传学方法,对李嘴墓地的79例个体进行了性别鉴定,其中男性33例,女性46例,男性个体数与墓葬数一致。全基因组分析结果显示,李嘴墓地33例男性个体的Y染色体单倍群具有单一性,说明他们出自同一父系。Y染色体仅存在于男性个体,只由父亲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儿。李嘴墓地46例女性个体的线粒体单倍群具有很高多样性,说明女性多种来源。线粒体为母系遗传特点,在一个家庭中,儿女与其母亲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群,女儿再将该线粒体单倍群传给其后代,儿子不遗传线粒体DNA。该报告综合亲缘关系评估结果、单亲遗传标记(线粒体单倍群和Y染色体单倍群)、性别鉴定结果,构建了该墓地的家族谱系及谱系示意图。墓地的第一代(一男二女)生育了四个男性后代,第二代四个男性及其后代分别构成A、B、C、D四个分支,整个墓地共有7代人。研究报告根据重构的家族谱系绘制了墓葬分布平面图。
我在阅读报告过程中,发现家族谱系示意图和根据家族谱系绘制的墓葬分布平面图里存在一些问题,如报告确定的第二代4例男性个体的长幼(即兄弟)关系没有任何依据,据推定的“第二代长幼关系”绘制的墓地分布平面图,不符合“昭穆贯鱼葬”;第五代男性个体中有一例携带的线粒体DNA,在上一代所有女性个体里没有找到这种线粒体DNA,也就是说,这个男性墓主的母亲没有埋在这处墓地里。该报告重建的家族谱系将这个墓与上一代墓葬做的谱系关联没有任何依据,报告对该墓及其下一代在墓地位置的理解也值得讨论;墓葬分布平面图中个别墓葬的辈分排错了。
我根据该报告提供的性别、配偶、辈分关系,参考明代随葬墓志的墓地,如江苏无锡青山湾明黄钺家族墓(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青山湾明黄钺家族墓》,《考古学集刊》第3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按“昭穆贯鱼葬”规则,首先确定李嘴墓地第一代(祖位)墓葬,这对夫妻(一男二女)生育的四个男性,埋在第一代男性左下方(昭位)的分别是长子、三子,右下方(穆位)的是次子、四子。这里的“长子”与“次子”,是依据出生时间先后,还是依据他们母亲的妻妾身份,值得研究。以第二代4例男性个体分别关联了第三代至第七代的男性个体,形成四门支派。我做的墓地布局结构图,还应受到随葬品等方面的检验。
通过学习李嘴墓地出土人骨DNA分析研究报告和参加项目验收会,我认识到:第一,不论是历史考古研究,还是人骨考古研究、DNA考古研究,都离不开坚实的田野考古基础。第二,历史考古结合人骨考古所推定的死者亲属关系,有较大的推测成分,只有引进DNA考古学研究,才能够比较准确判断死者亲属关系。第三,DNA只能确定死者的性别、配偶和辈分,同代长幼关系无法通过DNA判定。第四,DNA考古研究依据重建的家族谱系复原的墓地布局结构,离开考古学的时空框架与埋葬规则,就会出现方向性错误,如同没有层位关系的陶器类型学研究。第五,DNA考古研究替代不了人骨考古研究,解决不了诸如年龄、身高、健康状况、行为习惯等方面问题。第六,应当引进多种稳定同位素研究,尤其是46例女性个体的研究,使这个案例研究更加深入透彻。
李嘴墓地的33例男性个体和46例女性个体,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属性,需要把生物人与社会人结合起来进行墓地研究。从墓地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父系大家族里,男人娶老婆、纳妾、养外室;女人嫁夫生子,繁育后代;女儿随娘改嫁入后父家,再嫁后父子。同祖四门各不相同,有的支派繁茂,有的支派凋零。这处墓地清晰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一夫一妻多妾”,以及家庭之外隐秘存在的“外室”,即没有法律地位与家族认可的女性。墓地的布局与葬俗构成一个“社会剧场”,在生与死的空间,展演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与伦理,墓地布局结构就是费孝通说的“差序格局”物化表现。